得先叫他彬哥,不然这小弟娃儿定开口管我叫“兄弟”,还得是撞上他开心的瞬间,不开心时被他刺儿得体无完肤,只能自认倒霉,偏刺儿了人后的他的心情一百八十度云开雾散,得意地笑着跑开,嘿嘿,又赢了一盘,气得你呆立在原地顿足捶胸,无可奈何。某年回国,他们提起毕业二十年同学会,彬哥自爆猛料,张锦老师说对他,化作灰都认得,师生同心,某和张老师爱恨交加的咬牙切齿心有戚戚。
成都话的酥麻不仅在语音,还在词义,比如女孩子,上海人口中的“囡囡”打从出生用到大约九、十岁的样子,然后换了“小姑娘”直到出阁;在成都话里,“妹儿”的绵柔和甜糯可以用几乎一辈子,而这“小弟娃儿”的叫法不乏对家中幺儿的宠爱、包容与放纵,在初86级2班五十六个人的大家庭里,用在彬哥身上,恰到好处。
袁静说起彬哥,立刻提及初中毕业照中的影相,彼时身高尚未冲刺的他站在最后那排座椅上,微侧着身子,倔强地扬起下巴,三分桀骜不驯,五分玩世不恭,一分戏谑的少年老成再加一分不知天高地厚的狂妄,影相虽有些模糊,性格却那么鲜明。对对对,就是这个样子,众人颔首,三十多年过去,大家伙记忆犹新;竟被当面点评,口口声声说青春就是用来埋的彬哥万般无奈,童年怎么还没被埋干净?谁让你是班里第一个向姐发起挑衅的人,桌对面的我窃笑,终于可以为那些年被咬得咯咯作响的后槽牙报仇雪恨。
从童年到小少女的变化似乎是迈进中学校门的一刹那,就连我这打从上幼儿园起就和男生打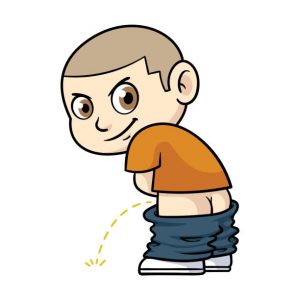 架的都一夜猛醒,男女生之间多多少少得避点儿嫌了,武力值悉数收敛不说,一言不合的追逐打闹也得全部戒掉。“是大姑娘了。”迈进七中校门前,父亲的提醒不无轻重;至于年龄比我小、个头儿比我矮的小男生,如彬哥、小李晋和周卓,一边儿去,光吃饭不长个儿的地转转,啥时候个头儿能赶上姐,再来和姐攒牙巴劲;偏二班三大天王里的两位,彬哥和周卓都不信邪,三天两头挑战我的底限,同一个大组,周卓有我最喜欢的组长袁静管着,彬哥则不然,用什么方式挑衅班里这些莽大汉儿的女生,得看人、看时机,还得看他当时的心情,那瘦小身子上顶着的大脑袋里到底装着多少鬼主意,无法统计。
架的都一夜猛醒,男女生之间多多少少得避点儿嫌了,武力值悉数收敛不说,一言不合的追逐打闹也得全部戒掉。“是大姑娘了。”迈进七中校门前,父亲的提醒不无轻重;至于年龄比我小、个头儿比我矮的小男生,如彬哥、小李晋和周卓,一边儿去,光吃饭不长个儿的地转转,啥时候个头儿能赶上姐,再来和姐攒牙巴劲;偏二班三大天王里的两位,彬哥和周卓都不信邪,三天两头挑战我的底限,同一个大组,周卓有我最喜欢的组长袁静管着,彬哥则不然,用什么方式挑衅班里这些莽大汉儿的女生,得看人、看时机,还得看他当时的心情,那瘦小身子上顶着的大脑袋里到底装着多少鬼主意,无法统计。
第一节班会课上,张锦老师问有谁认识全班同学,我举了手。以我一贯的耿直,但凡举手,成竹必在胸,答案没准儿会错,但高举的右手和倔强的性格一样,不退缩。全班竟只有我一个举手的,远处传来一个隐隐的声音,似乎是从牙缝里蹦出来的“颤翎子”,正当我扭过头去想要计较时,身后另一侧传来一个质疑的声音,“你认识全班人啊,那我叫啥子名字?”
“你叫X彬。”我回过头去,十足把握,小弟娃儿,第一天上课我就认识你了,瘦瘦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耳朵有点儿小招,并不明显,分明一张可爱的少年脸,阳光灿烂的笑容下却总是藏着坏坏的小心思,让人心里难免有些发毛。
彬哥做了个鬼脸,答对了。
没想到,那以后这个圆脸的小弟娃儿总时不时地挑战十三四岁的我尚不够坚强的神经,重复、反问、引用、质疑、打趣、反诘,等你咋么过味儿来发觉自己被针对时,他早已领先一步察觉你即将发怒的情绪,开心地摇晃着那圆圆的大脑袋,得意地坏笑着,先行撤离,就那属耗子的灵敏度,想追上去武力解决根本没机会。别说我没机会,就连个儿头比我高、跑得比我快的王菁都没有机会。
同学群里有个经典旧事,话说当年彬哥不知怎的惹了王菁,王菁追上去想打回来,彬哥一下子跑进办公楼里,得意洋洋,你打我啊,打不着了吧,嘿嘿嘿。办公楼从来都是同学间追逐打闹的禁区,王菁无奈,只好作罢。日后提起,王菁每每佯怒,彬哥总是得意,那坏笑分明还在挑衅,“那么大的个儿都打不着我,嘿嘿,嘿嘿。”
我是打过彬哥的,在记忆里,不过好象不是主动打的,是受了邀请。彬哥说不可能,他那时那么灵敏,怎么会没逃掉,且以他的机智,又不是拿抓(哪吒),怎会邀我去打他。但我脑子里始终有一组镜头,先是彬哥坏笑着,一次次歪着头,冲我扬起下巴,“你打我啊,你打我啊。”接着切换到周围几个同学惊讶的眼神,尤其是子茹满脸的惊愕,我是真的动了手?我心虚地嗫嚅着,“他邀请我打的,他邀请我打的。”我那时到成都应该已有四五年的光景,初到时在市中心茶铺里跟老街坊们学的成都话音调虽标准,放学回家立即调回普通话频道的缘故,对方言的理解力依然得靠普通话的嫁接;以彬哥土生土长的四川话水平,早超越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四川馍馍”,什么“豁皮”,“丘八儿”,“闷墩儿”、“曲波”常被他挂在口中,好些都是我离开四川多年后仍搞不懂的俚语,既然他一遍又一遍热情洋溢地邀请,却之不恭。后来彬哥说我一定是记错了,可我偏偏记得当时分明是盛情难却,至于是正中目标还是只擦着衣袖,记不清楚了。
有一年冬天,不记得是初二还是初三时,还没到备战期末考试,成都竟下起了雪。彼时的细雪像极了成都平原慢吞吞的生活节奏,那颤颤悠悠飘在半空的雪花自是无法抚慰我的乡愁,地温高的缘故,着陆的雪花瞬间悄无声息地钻进大地,被小花园里冬青叶半道拦截的,充其量是些许的晶莹,遇到女生小心翼翼的试探,顷刻间化作雪水,滴落。面对我的不屑,子茹说虽比不上你们西安的琉璃世界,已经令在冬天里不大能见着飘雪的四川孩 子开心老半天了。所谓乐极生悲,当天就被紧急加开班会,据说是我们班的男生爬到学校厕所的房顶上去采雪。那可是五十年代初修建的厕所,房顶上的水泥瓦没准儿三十年间都不曾换过,这么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除了咱班的三大天王还能有谁?一想到课间操后不久被彬哥视若珍宝地捧在手心里把玩的小雪球,那叫一个恶心;班主任张锦老师的操心可不一样,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一群初中小男生攀爬到学校厕所的房顶上,在一层薄雪上傻乐呵地采集,一点点积少成多地攒雪球,那大呼小叫的兴奋劲儿,生怕路过的老师同学不知道是我们初86级2班的傻小子,摔下来怎么办,怎么和你们的父母交代……后来我每每想起他们几个在房顶上采雪的画面,就很理解83年秋天刚接手2班时张锦老师的担忧,这个班独生子女、幺儿幺女太多,不好带,以张锦老师当年的全情付出,遭遇班里这群调皮捣蛋鬼日日更新的顽皮花样,消耗的怕不仅仅是发量,还有……
子开心老半天了。所谓乐极生悲,当天就被紧急加开班会,据说是我们班的男生爬到学校厕所的房顶上去采雪。那可是五十年代初修建的厕所,房顶上的水泥瓦没准儿三十年间都不曾换过,这么脑洞大开的奇思妙想除了咱班的三大天王还能有谁?一想到课间操后不久被彬哥视若珍宝地捧在手心里把玩的小雪球,那叫一个恶心;班主任张锦老师的操心可不一样,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一群初中小男生攀爬到学校厕所的房顶上,在一层薄雪上傻乐呵地采集,一点点积少成多地攒雪球,那大呼小叫的兴奋劲儿,生怕路过的老师同学不知道是我们初86级2班的傻小子,摔下来怎么办,怎么和你们的父母交代……后来我每每想起他们几个在房顶上采雪的画面,就很理解83年秋天刚接手2班时张锦老师的担忧,这个班独生子女、幺儿幺女太多,不好带,以张锦老师当年的全情付出,遭遇班里这群调皮捣蛋鬼日日更新的顽皮花样,消耗的怕不仅仅是发量,还有……
初二那年我迷上了打乒乓球,因为父亲生病的缘故,正好找借口在学校搭伙,饭后和李萱一起打乒乓球。那时最不能忍受的是上午第四节课的老师延堂,但凡被延堂,就会在课桌里猛晃装了勺子的饭盒,催促老师赶紧收工下课。因为下课铃一响,就会有同学冲出教学楼,抢占办公楼南侧出口和厕所间空地上的乒乓球台。七中那时有六个水泥做的乒乓球台,靠近教学楼一侧四个,靠近综合楼一侧两个,我们班的教室在校园南侧,离乒乓球台较近,下课铃响前五分钟,我已经准备好拿着球拍和饭盒一起冲出教室,把球拍往空着的球台上一放,占好球台,再拿起饭盒快步追赶李萱去食堂排队的脚步,吃完饭,开战。彬哥那会儿也在学校搭伙,午饭后的他偶尔会晃着大脑袋过来观战。我和李萱那时的对战通常是21分为一局,三局两胜,天天午后一起打球,竞赛很快就演变成棋逢对手的切磋。彬哥起初笑嘻嘻地在球台边观战,也不言语,看一会儿就跑了,后来会趁我俩中无论哪一个有些倦意时,提出让他玩一下的请求。外人的加入,自然不会是我和李萱约定好的21分法则,3光4K,彬哥也不计较。只是球拍到了他手里,那叫一个戏多。方才老老实实观战的小弟娃儿立刻换了个人,还没发球,坏笑已经挂脸上了,但凡白色的小球在他手里,他会得意地冲你笑笑,先“通知”你接球后球的走向,然后轻轻地抛起球,也不是很高,球拍接触的瞬间手腕猛一抽,白色小球以飞快的速度旋转着就过来了,接球的瞬间,小球回旋的方向真被他说中,且飞离了球桌,就这样被他轻轻松松抢夺了我俩在乒乓球台上的控制权,反客为主,直打到他不想玩了为止。好在李萱快速反击的打法没几个星期就破了他发球的优势,被打败的他依旧笑嘻嘻地晃着大脑袋离开,愿赌服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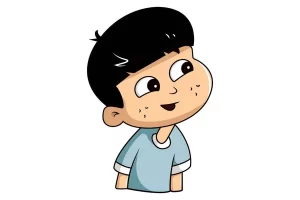 对乒乓球的痴迷常常是放了学还留在学校里打球。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李萱在球台前激战正酣,彬哥跑过来,“你爸妈来找你了。”我不假思索地挥着球拍追了过去,费头子,想蹭球打直说就是,拿我爸妈来说事儿,不打你一顿看来今天你我都过不去。中学六年,父亲病了五年半,行走困难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病休,只好一边上着班一边遍访名医。双职工的优势,母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心,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的身体,陪着他看病,陪着他出差,家中的日常通常是我们早上上学后,所里派几个壮小伙子来抬着父亲去上班,下午的时间父亲不是在做看病,就是在做治疗,得到的诊断怀疑是类风湿,未见恶化却也不见好转,父母依然每周三次从所里慢慢走到学校对面的六路车起点站,辗转着去交子街看老中医。因为年少的敏感脆弱,家里的事我从不在学校提及,就连子茹春曦也只是隐隐地知道,没想到这调皮的天王竟敢谎称我父母来学校,一时间愤怒将我点燃,铁了心要狠狠地收拾彬哥一顿。
对乒乓球的痴迷常常是放了学还留在学校里打球。有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和李萱在球台前激战正酣,彬哥跑过来,“你爸妈来找你了。”我不假思索地挥着球拍追了过去,费头子,想蹭球打直说就是,拿我爸妈来说事儿,不打你一顿看来今天你我都过不去。中学六年,父亲病了五年半,行走困难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病休,只好一边上着班一边遍访名医。双职工的优势,母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事业心,服从组织安排,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的身体,陪着他看病,陪着他出差,家中的日常通常是我们早上上学后,所里派几个壮小伙子来抬着父亲去上班,下午的时间父亲不是在做看病,就是在做治疗,得到的诊断怀疑是类风湿,未见恶化却也不见好转,父母依然每周三次从所里慢慢走到学校对面的六路车起点站,辗转着去交子街看老中医。因为年少的敏感脆弱,家里的事我从不在学校提及,就连子茹春曦也只是隐隐地知道,没想到这调皮的天王竟敢谎称我父母来学校,一时间愤怒将我点燃,铁了心要狠狠地收拾彬哥一顿。
“真的,儿豁你!”彬哥一边逃跑,一边指着另一个方向,“就在那儿,你切嘛,儿豁你。”
虽然愤怒,对彬哥的性格总还是了如指掌的,他虽顽皮,虽然爱惹事,口头上却绝对不肯吃亏,只有他滑头地占别人的便宜做“老子”,哪儿有他自称“儿”的时候?还一下子两个“儿豁你”。
我将信将疑地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跑去,没几步,就看见母亲扶着颤颤巍巍向我走来的父亲,那一刻,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年少的脆弱,会觉得学校是逃避现实的乐土,父亲的病,母亲的难,仿佛一背上书包就可以抛之脑后,如今一切被真实地摊在同学面前,还是被这么个总是挑战我敏感神经的“反对党”来通知的,明天又会被他当着大家的面怎样取笑……来不及思考,只飞快地抹干眼泪,冲过去和母亲一起扶着父亲站稳。
学校不一样了,父亲感慨,这是他的母校,初中毕业时自己搬着桌椅从青龙街搬过来的母校,三年高中时光,多少快乐的记忆;还是那个格局,校门口的小树早已参天,爬山虎也爬上了教学楼,七里香的花廊好像是新修的,男生宿舍一点儿没变,连后门边食堂的门窗都还是原来的颜色……回家后,父亲提起那个领他们来找我的小弟娃儿,很聪明的样子。
调皮得很。我皱着眉头,满脑子都是明天面对彬哥调笑时该如何应对。
调皮的孩子聪明,父亲坚持,多好的孩子,正玩得起兴,一听说我们找你,立马自告奋勇地带路,很热心。
紧接着,父亲想起了什么,可不能欺负人家哦。
完了,不久前好像刚揍过彬哥,他邀请的,一而再,再而三。
父亲皱眉,说了多少遍,恃强凌弱绝不可以。
……
我好像并没正经八百地去给彬哥道歉,第二天他也没拿父亲的病取笑我,后来我猜许是那圆圆的大脑袋当时压根儿不记事儿,只是父母和我,都不曾忘记。此番回国,每次向母亲展示同学聚会的照片时,母亲总第一时间认出的一定是彬哥,那个多可爱的小弟娃儿,聪明,热心,记住,你爸说过,不能欺负他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