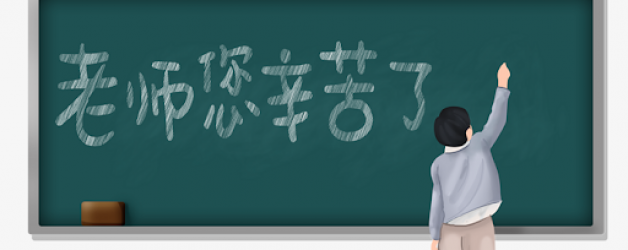回忆七中往事时我总在想,教师这职业,尤其是语文老师这活儿,技术含量其实挺高的。同样是字词句段篇的教授,学英语的动力是出去看世界,而语文老师在教书育人的同时肩负着“文如其人”、“文以载道”的职业使命,没有大量的知识储备,怕很难应对成都七中的课堂上那一双双渴求中掺杂些许挑剔的眼神,生源大都来自周围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优势是学生的学习能力和领悟力都较强,劣势是他们从原生家庭里多少会带来些知识分子的清高,孩子王不好做。
我的运气是初中时遇到力争上游的张锦老师,高一时被慈母心满满的胡衡影老师温暖,进了文科班被文仲瑾老师打通任督二脉,此三位恩师的教导,终生难忘。
张锦老师接手我们老二班时不到三十岁,那时的她的学识和心智估计尚未达到文仲瑾老师口中“一桶水”的储备,应对十二三岁的我们应该足够。如今想来,记忆中许多清晰的片段竟大都停留在老二班的语文课上,除了“的地得”的讲解精准到位,张锦老师讲词语的内涵和外延时在黑板上顺手画的大小两个圆圈简明扼要;还有讲统筹方法的那节课,枯燥的说明文竟能被她精准地诠释 “磨刀不误砍柴功”;《论语》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与家父坚持的“主雅客来勤”虽不谋而合,但在八十年代居住条件有限且自我意识萌芽的我看来,“乐”还是有条件的;至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更是和听着军号长大的我从小接受的“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矛盾重重,是文化变了形还是时代走了样,要教育我这多思的学生真不容易。
语文的教学在中学课本里从来不乏政治教育功能,比如老三篇里的《纪念白求恩》,张锦老师朗读文章最后那段话时铿锵有力的调门儿我至今记忆犹新,“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课文中的白求恩大夫对我而言是当年在延安给爷爷做手术的人,因为医疗条件有限,没取出来的几块弹片终导致爷爷依赖酒精的麻痹止痛,那个性情温和的老人,那个战争绞肉机的幸存者,没能等到和全家一起分享孙女考进七中的喜悦,所以我的骨子里从不接受造神;对张锦老师而言,那个高尚的,纯粹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且有益于人民的人,应该是五十年代生的他们在停课闹革命的岁月里最早树立起来的指路明灯,从瘦小的身躯在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站在成都七中的讲台上,这盏灯支撑着他们这代人……我的语文课总在这样的天马行空中偏离了航道。
在鲁迅的文章大量充斥中学语文教材的年代,民国文人的口诛笔伐着实让人耳目一新,从家中的藏书中窥见梁实秋先生的散文之美后,接受左翼文风变得难上加难。以当时的幼稚,打笔仗也该顾及些斯文,指名道姓地破口大骂与鸳鸯蝴蝶派笔下的民国难免违和,写写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描描吃茴香豆的孔乙己,损损豆腐西施杨二嫂,回忆一下盼新年盼闰土的心情,哀一下吃人血馒头的,何苦让带着火药味的唾沫星子满天飞。
除了文学大观园的步步引领,老二班语文课堂上不乏趣事,那天学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张老师的抑扬顿挫和声情并茂愣是带着我们这些长江上游生活的少年见识了中下游的大河浩浩荡荡,横无际涯的壮观。尤其是“至若春和景明”那段,于淫雨霏霏的阴霾共情一下子高抛到“上下天光,一碧万顷”的明丽欢快,到“岸芷汀兰,郁郁青青”时突然打住,提醒大家,班里这个叫李汀的同学的大名应该是汀,而不是丁,不要你们平日里错别字读惯了,将错就错地“丁”字读到底,汀就是汀,丁就是丁。那一刻全班静悄悄的,我费了好大劲才憋住笑,平日里那么严肃的张锦老师上课时也会有这般自由的跳脱,性情中人。
升入高一后不幸被分到五班,数学老师朱齐庄做班主任,就差把“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真理”刻脑门儿上了。高一五是个神奇的班级,因为揽入了四川省数学竞赛冠军石伟,全班都象是在陪太子攻书,无论是外校考入七中的尖子生们(俗称油面子),还是象我们一样从初中直接考回本校的老油条,大家对朱老师踩着每天下午第二节课下课铃进来狂书几大黑板数学作业的蛮横似乎都毫无怨言,唯一听到的抱怨是针对教语文的胡衡影老师,坐在我后面的石伟张韬时不时地讨论胡老师白开水式的教学有多辜负他们对七中名师的期待,抱怨高一语文的教学大纲设计适合混日子的老师,抱怨语文课的枯燥无味让他们有多想在课堂上打瞌睡……但瞌睡虫是会传染的,我的语文课也被害得睡意沉沉,直到有一天胡老师讲修辞,嘴里蹦出“真他妈的好啊”,我才被惊醒,原来语文可以这么教。
胡衡影老师的教学方式和张锦老师的路数迥异,如果初中三年是和张锦老师一起成长,那么高一的一整年是被胡老师带着体会四平八稳的中庸之道。胡老师的影像是磨子桥地区典型的女性中年知识分子,四十多岁的年纪,瘦小的个头,卷曲的短发,脸上永远是温和包容的笑意,是学校里的老师,更像是邻居家的妈妈。翻开旧相册,我的七中六年里只有一张和老师的合影,就是和胡衡影老师在一起,那是高一的春游,全年级去爬青城山,我们班借的卡车坏在西门车站附近,直等到大家在车里把带着的干粮吃完后才修好,开到青城山脚下时留给登山的时间所剩无几,在跑上跑下的登山和就地打发两三个小时的选项中我们这群人拔腿就往山上冲,登顶后再急吼吼地跑下山,哪里是春游,分明是拉练。和胡老师的合影好像是在上清宫附近的一个摄影点拍的,照片中的我笑得灿烂,身后的胡老师一脸温柔慈爱,只被她外套下有些凌乱的衬衣领口泄露了拉练的强度。当时拉着胡老师拍下那张照片,是因为被朱齐庄的题海战术搞得终日阴霾的高一,胡老师批改周记的细心认真带给我唯一的快乐。
高一的语文写作训练目标是散文,每周末都有周记的作业要交,字数常常定在五百。写作的训练在初中时是记叙文、说明文和议论文的循序渐进,可惜哪一种文体我都没摸着门道儿。记叙文看似很简单,可一想到上课时分析的那些中心思想、主要内容,耳边难免响起“白开水”、“王大娘的裹脚布”之类的评论,再看看写过无数遍的《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一件小事》的命题,面对稿纸时徒生一种才思枯竭的无力感;记叙文都写不好,说明文就更不知该如何着墨,家父说多看几篇技术文章就能开窍,可他的经验无非是另类安眠药;至于议论文,论点立不起来,论据漏洞百出……散文我是喜欢的,这种“形散而神不散”的文体虽然读初中时无法掌握,到了高一,在每天拼命逃离几大黑板立体几何作业的压制下突然开了窍,周日晚上独坐桌前,关上灯静思片刻,提笔,十点熄灯前一气儿干完五百字,压根儿不用数格子。周一交好作业后就开始盼着周记本发下来,那本子上胡老师用红圆珠笔书写、勾划的点评总能让我有所受益,哪儿的措辞有待推敲,哪个句子出彩,哪段描述不足,哪里情感到位,什么地方转接太陡,整篇文章的观感如何……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受到这样的礼遇,我的心里暖呼呼的,本以为不过是静思后的文思冲动,却被那红色圆珠笔下字斟句酌的圈圈点点慢慢地校正写作的轨道,因为胡衡影老师的悉心呵护,我在高一时喜欢上了散文的自由。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传道和授业被张锦和胡衡影二位恩师兢兢业业地实践后,进文科班遇到文仲瑾老师,才算是真正解了惑。人生之惑大约始自十五六岁的年纪,在那个迈向成年的岁数,再无忧无虑的岁月中也难免会掺杂些对未来或憧憬或迷惘的遐思,再一帆风顺的人生都要面对生存的现实,迈出校门后的日子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灿烂,该如何应对,文老师亦师亦友的指引让我受益终身。
提起文老师大语文课的坚持,文科班的同学没有不竖大拇指的。和张锦老师的热情上进,胡衡影老师的温暖如春不同,文仲瑾老师应该是那些考进七中的外校尖子生们真正仰望的七中名师,学富五车,做文、做人、做先生,样样都令人打从心眼里佩服。文老师的语文课教授的不仅仅是教科书上应对高考的篇章,更多的是观察生活的技法和应对周遭事物的态度。高八九级六班的同学不知几人还记得星期六上午最后的那两节语文课,那是文老师专属的大语文课,通常是抛开教材,这个星期写作文,下个星期畅聊天地。我记得有一节畅聊课上聊到成都话里的“尿巷子”,文老师问有没有同学知其意,教室里没有回应,就连我这在市中心老茶铺里学的成都话都一脸懵,文老师随即解释是离大街较远的背街小巷,不长,在公共厕所难寻的年代……我的脑海里立刻闪现出暑假的清晨陪奶奶去东城根街菜市场买菜时常见的画面,那些自行车两边搭着巨大的两个竹筐进城卖菜的市郊农民着急忙慌地把摊子暂托给旁边的人,快步冲进附近早已觅好的一条短短的死胡同,一转身……成都方言里竟有如此鲜活的表达法,有趣。
那个叛逆的年纪开始和父母的世界观产生分歧,当“人一上百,形形色色”的老话儿从文老师那儿不经意地流露出来时,突然领悟这世界远不只一种正确的标准,既然一样米养百样人,百样人就值得拥有百样色彩,一时间,我心中早已固化的非黑即白的世界观动摇了,慢慢领悟了尊重差异的智慧,这智慧伴我几十年间随时矫正对人、对事的态度,提醒我欣赏差异之美是成年人必备的修养。家父常说读书得从厚读到薄,可有时书读得再厚也不过是量的累积,质的飞跃需要睿智的人指引,文仲瑾老师就是这样的良师。
进文科班之前,文学对于我而言高不可攀,是托尔斯泰,是唐宋八大家,是司汤达,是莎士比亚、是《红楼梦》、是《牡丹亭》、是《战争与和平》、是《巴马修道院》……小说看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似乎只有扣紧某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方能沾上文学的边。遇到文老师后才明白,每一个时代都是大时代,文学并不只是高不可攀的长篇大著,是源于生活的每一个精彩的片段,每一份真挚的情感,每一分仔细的观察,每一次认真的思考,每一个字、每一句话、每一次推敲后都可能成就文学,文学无需被仰视,只需拿起笔来,记录、打磨;文老师坚持要给学生一杯水,老师得有一桶水的储备,我于是常常猜想文老师的那桶水里都藏着些什么?文学、风骨、生活、睿智、爱心……
在文仲瑾老师带的文科班里,写作是一件快乐的事情。上高二不久,我们就接触到微小说的写作,这个类型对我而言既兴奋又惶恐,不到千字要讲述一个故事,够完整又不能罗嗦,有节奏又得有逻辑,这可不是十几二十分钟的静思能完成的活儿。构思好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后,我果断地从关键情节切入,大刀阔斧地削砍裁减,最终得到文老师的表扬,说看到我写小说的潜力。当我兴高采烈地把文章拿回家给拒绝被我的文字烧脑的父亲看时,父亲颔首,“有那么点儿意思。”说明文的写作紧随着那篇微小说一通百通,就只剩下议论文的堡垒。一次大语文课上,秋子、欣然、智斌和我正激烈地讨论某话题,站在一旁倾听的文老师突然看着我若有所思,“辩论时滔滔不绝的嘴皮子怎么写议论文反倒不行?”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原来议论文就是把辩论时的脑回路通过笔尖放到格纸上去锤炼啊,那以后再也没难得住我的文体。
毕业后因为张彦家住七中的缘故,我常常在七中宿舍区的小门出入,有一次在门口遇到正在小憩的文老师,上前和他打招呼,他一怔,问我是那个年级的学生,我笑着说八九级,六班,心里难免失落。多年后释然,桃李满天下是老师的职业特点,记不住学生实属正常,只是作为学生,无论学识的累积还是智慧的启迪,当大门被老师们亲手打开,一路护航,此恩此情,终生难忘。